文 | 中信出版集团
今年两会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明确指出:今年不设全年经济增速具体目标。受疫情影响,经贸形势不确定性较大,目前主要引导各方面集中精力抓好“六稳”、“六保”。这一说法立刻让很多人觉得,用GDP衡量经济增长是不是已经过时了?
其实早在两会前夕,就有不少经济学家建议淡化经济预期目标,转而关注更多民生类指标。“内外部都有很大的不确定性,这时候简单地看GDP指标是没有可比性的。”国务院参事室特约研究员姚景源说。
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,设定年度GDP增长目标的做法就沿袭下来,在发挥经济发展“指挥棒”作用的同时,一些消极影响也逐渐显露。近几年,放弃“GDP竞赛”的呼声越来越高。此前召开的地方两会上,广东、江苏、浙江等大多数省市都将其GDP增长目标由锚定某个固定数值,改为设定一个目标区间。
姚景源曾担任国家统计局总经济师,参与过一系列经济指标的制定和统计。在他看来,在中国经济总量逼近100万亿元,外部环境存在巨大不确定性的特殊时刻,更要讲究增长的质量。“这也许是一个契机,让我们逐渐淡化GDP指标,更加重视全面脱贫、贫富差距、就业保障、市场活力等指标。”
这一观点与近日由中信出版集团出版的新书《增长的错觉》一书中对于GDP的看法不谋而合。《增长的错觉》作者戴维·皮林作为英国《金融时报》的获奖记者与编辑,他引导读者探索了人类对经济增长的痴迷。他在书中指出,经济增长只是实现目标的途径,而非目标本身。人们一直通过经济增长这块棱镜看待一切事物,而这个习惯扭曲了我们的视线,使我们忽略了真正值得关注的事。
书中深入探讨了其他衡量经济状况的可能指标,比如社会平等、环保以及人的幸福程度等,为社会回应人的真实需求,提供了一个看待GDP的全新视角。
GDP的局限
在作者看来,GDP的过人之处在于它把所有人类活动压缩成一个数字,如同将一只大青蛙挤进一个火柴盒里。这样看来,GDP的确可以称得上是人类的伟大创意,并提供了一些有用的信息。它使我们看到一种现实的全景,使政治决策者做出相应举动。但这种“聚合”既是GDP的美感所在,也是 GDP 的一个缺陷。一个数字无法捕捉人生中一切有价值的东西,就连经济学家的人生也不例外。
对于GDP,作者保持着作为记者具备的“质疑精神“,并提出了这样一个从实际出发的终极问题:既然GDP存在一定的缺陷,究竟什么指标可以替代 GDP?
到目前为止,无论从强度还是广度而言,其他经济衡量指标均无法完全替代 GDP。因此,这个问题的答案是,与其寻找GDP替代指标,倒不如寻找能够对GDP做出有益补充的指标。这样,我们就能靠这些指标勾勒出一个更为准确的全球经济图景。
1.人均GDP
用GDP除以国家人口总数得出人均GDP的做法,可谓是对GDP进行的一种最便捷的调整。但人们很少这么做,至少大众对人均GDP的关注仍然较少。人们依旧习惯用GDP这一总量的绝对值来表示经济增长,而未将人口基数的增长考虑在内。
如果一个国家的GDP增速为2%,但该国人口同样增长了2%,那么其人均 GDP完全没有变化。投资者经常对一些发展中国家的GDP增速感到欢欣雀跃,却忽略了这些发展中国家的高生育率。增加一个国家的经济总量的最简单的办法便是增加人口。如果特朗普有意实现3%的GDP增速,那么这将是一个再简单不过的目标。他只需要将美墨边境之间的墙拆掉,每年让1000 万墨西哥人涌进美国即可。但特朗普需要的不是3%的经济增速,而是3% 的人均GDP增速。这完全是另外一回事,而且是一个更加难以企及的目标。
在经济学家的世界里,如果一个国家永远不增加劳动力,那么它不大可能实现经济增长。正因如此,许多经济学家才称日本陷入所谓的“民主死循环”——其人口数逐年递减,但人均GDP倒一直维持着正增长。
经济学家们无比推崇“经济必须持续增长”的观念,却发现自己难以打破“单靠加人来拉动增长”的逻辑。倘若马尔萨斯认为人口基数的日益庞大终将使人类文明走向灭亡,那么当今时代的经济学家们的想法恰好与马尔萨斯相反。
不过,鉴于全球人口不会无限增加,全球经济恐怕也终有停止增长的一天,至少对某些发展成熟的富裕经济体来说是这样的。但这并不意味着人均 GDP一定会停止增长。给予人均GDP更多关注,将是人类踏出的重要一步。这一步虽小,但能使我们在政策制定的过程中真正做到“以人为本”,而非仅仅顾及“经济”这一抽象概念。
2.收入中位数
这一指标甚至比人均GDP更值得关注,它具有一个大优点和一个小优点。大优点:它计算的是收入的中位数而非平均数,但人们经常搞不清两者的差别。假设有一个四人组成的社会,人口总收入为100美元。倘若只有一人有收入,那么收入的平均数为25美元。《金融时报》首席统计学家基斯·弗雷曾在员工大会上讲述了这样一则笑话:“如果比尔·盖茨走进一间酒吧,那么在场每个人的平均收入都能达到亿万富翁的水平。”作者后来才了解到,统计学家的“幽默”源于这样一个事实——平均数不过是总收入除以人口总数后得到的数字。若我们使用不慎,那么它会让我们对现实的理解发生扭曲,因为平均数并不能让我们看到收入的具体分配情况。随着社会不平等程度的加剧,这个问题正变得日益突出。
不同于平均数,中位数相当于让所有人站成一排,然后挑出站在最中间的那个人。收入中位数使我们得以大致确定普通人的收入有多少,因而也可被称为“中产阶级收入”。在这个年代,中产阶级常感觉自身被社会遗忘和误解,因此这个能够代表该阶级收入水平的数字,将对改善该阶级的境况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。
收入中位数还有一个小优点,即它针对的是收入,而非生产。
对大多数人而言,收入比生产更容易理解,因为人们更常思考的问题是“我靠什么生活?”,而非“今年生产了多少辆叉车?”。国民收入理论认为,人们只能购买生产出来的产品和服务,而生产多少产品和服务又由人们的购买力决定,因此,生产和收入应当等量,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。
主管美国GDP计算工作长达20年的史蒂夫·兰德费尔德同样是收入中位数的推崇者。但他表示,收入中位数呈现出来的信息恐怕会让一些政治家感到不自在。“可以说,任何一个国家的统计机构都难免对收入中位数有点儿忌惮。”他告诉我,“但我认为,美国与其他国家越来越认同一个观点,即我们有必要正视收入中位数。”
3.社会不平等程度
收入中位数也存在若干局限。因为除了确定普通人及其家庭成员的情况外,我们还需要了解那些社会底层人士的境况。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有好几种,其中的一种又快又好的方法就是运用基尼系数。基尼系数由意大利统计学家科拉多·基尼于1912年发明,其范围为0~100。“0”表示完全平等的社会,每个社会成员的收入是相同的;“100”表示极端不平等的社会,其中一个社会成员占据全社会的收入。相对平等的经济体的基尼系数低于30,而全球最不平等的经济体是南非,其基尼系数为63。美国的基尼系数为41,英国和德国的基尼系数分别为33、30。同理,基尼系数也可反映财富或资产在一个经济体中的分配情况,且其结果较收入的基尼系数更具差异性。另一种反映社会不平等程度的方法是按人口结构剖析收入情况。这种方法不仅能揭示收入的分配情况,还能揭示高收入人群与低收入人群之间的收入差异究竟有多大。
4.NDP(国内生产净值)
GDP衡量的是收入流,但我们也需要知道国家财富还有多少存量,否则就容易犯那个将“银行家比尔”与“园丁本”混为一谈的错误。近年来,美国经济分析局持续收集NDP数据,但在GDP的光环下,NDP几乎没怎么引起人们的关注。NDP减掉了GDP中资本品(如公路、机场和房屋)的折扣值。如果一个国家的资本存量增加,那么其NDP也随之攀升,反之亦然。NDP与 GDP之间的差值能提醒我们,一个国家是否透支其资本存量,用以刺激当前的经济生产。
布伦特·莫尔顿在美国经济分析局从业多年,一直是美国国民经济核算工作的负责人。他认为,NDP应受到人们更多的重视。“有关国家的一个根本问题是,其财富是在增加还是在减少?”
莫尔顿表示,对那些自然资源大国来说,计算国家财富意义重大。可即便是像美国这样的国家,想要实现经济繁荣,也得注意积累财富,包括基础设施、高等院校和自然资源等。对任何一个国家的国民经济核算工作而言,国家财富的积累都至关重要。只有那些NDP高的国家,才能实现国民生活水平的长远提升。
5.人民幸福水平
没有哪个GDP的追随者会承认GDP能够衡量人民幸福水平,但几乎也没人会否认,GDP已在不知不觉间成了人民幸福的代名词。
关于“幸福由哪些要素构成”的问题的答案,可谓“仁者见仁、智者见智”。但这并不妨碍我们计算幸福水平,定义和衡量幸福的过程有助于我们确定哪些事项应当优先发展。尝试衡量看似不可衡量的东西,比如幸福或某些更广义的社会福祉,都能使我们的思路变得更清晰。
一旦马里兰州的GPI获得更广泛的公众关注和政府支持,迎接它的恐怕就是一场激烈的争论。试想,如果州长因本州GPI下跌而发起政策改革,那么一些人将对GPI的价值拍手称快,并将GPI作为判断经济是否景气的标准;另一些人就可能会认为,GPI的衡量对象有误,因而GPI需要被其他更好的指标替代。无论如何,在衡量人民幸福水平方面的尝试势必会引发争议。它让我们反思自身所在社会的奋斗目标,并帮助我们监测社会在实现这些目标的路上走了多远
对于GDP,我们是时候向前看了
当我们一心追求更漂亮的GDP数字时,不能忽略一个同等重要的事实:我们不能沦为数字的奴隶。尺子之所以能够度量长度,是因为它本身也有度。并非一切事物都能被明码标价,也并非以美元为单位的东西就更好。这正是近年来西方国家的政治反抗事件让我们接受的教训之一。在这些事件中,选民们不甘沦为政治工具,而选择奋起反抗。
GDP的发明使一批技术专家和经济学家崛起。他们主张政策应以发展经济为导向,却因此忽略了千千万万劳苦大众的利益。他们沿袭了牛顿看待事物的方式,将经济视为一个理性、有规律可循的体系,一个各机械部件分工明确却又彼此连通的实体,甚至一种人类经验不可及的东西。一位具有独到见解的思想家写道:“数学使经济学焕发生机,却也使它不幸僵化。”
在GDP诞生前,“经济”一词从未进入政治家的视野,这在今天似乎是不可想象的。如今,没人认为经济是一个超越人类经验而独立存在的实体。1950 年之前,现代意义上的“经济”概念一次也没有在英国公开的政治文件中出现过。后来,这一局面随着GDP的发明而被打破。GDP就像一扇后门,使经济学家得以从这里偷偷爬上公共舞台,进而在政府与官僚体制中徘徊。
经济学家固然能为政策制定者提供宝贵的专业建议,但这些建议不是全部。政府治理的方式也不止一种。任何公共机构都没有必要解释自身行为能产生多大的经济贡献。例如,在国际上享有盛誉的大英图书馆就没必要证明,每收到1英镑的公众捐赠能产生4.4英镑的经济贡献。同理,某知名儿童慈善基金会之所以鼓励广大父亲给孩子读睡前故事,也并非因为这么做能提高儿童的识字率,进而使GDP在2020年上升1.5个百分点。安全的街道、体面的工作、清新的空气、开放的场所、社会归属感、安全感、幸福感,以及对书籍和阅读的热爱,在本质上都是好的东西。更高的收入有时能让我们得到渴望之物,有时却不能。但更高的收入和GDP本身永远都不应该成为我们追逐的目标,充其量只是我们实现目标的途径。库兹涅茨曾反躬自问:“增长的到底是什么?为什么要追求增长?”
我们对经济学家的唯命是从,源于“和物理定律一样,我们也无法违反经济学原理,即无论我们多么想做一件事,都不能忤逆所谓‘经济的’逻辑。”不过,我们有时还真能忤逆“经济的”逻辑,且有时必须这么做。经济并非实体,只是一种人类想象世界的方式。GDP也不是客观存在的物体,不过是人类为了衡量某些东西而完成的巧妙发明。以GDP为指针的经济增长纵然是人类历史上的一项伟大发明,但现在,我们是时候向前看了。
本文获中信出版集团授权发布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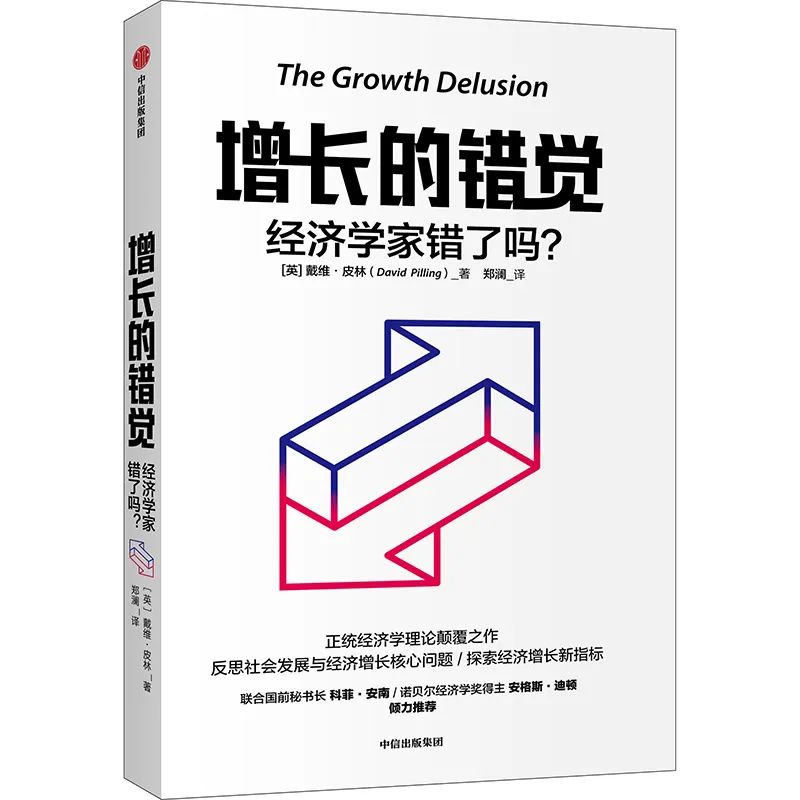
《增长的错觉》
作者:戴维·皮林
郑重声明:本文版权归原作者所有,转载文章仅为传播更多信息之目的,如作者信息标记有误,请第一时间联系我们修改或删除,多谢。


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