市场赚钱效应升温,风格却不断切换,抓住低吸潜伏的好时机!立即开户,踏准节奏,不错过下一波大行情
文人中的吃客大有人在,前有梁实秋,后有汪曾祺,各有各的特质,但兼顾饮食之道与学问之内里的唯有周作人。
周作人对于美食的钟爱,源自故乡,贯穿南北,在他看来,“看一地方的生活特色,食物很重要,不但是日常饭粥,即点心,以至闲食,亦均有意义”。羊肝饼、炒栗子、臭豆腐、猪头肉、瓜子鸡、瓠子汤、香酥饼、素火腿、萨其马……平生所尝,皆成文章,进而生发出背后的学问和世道人情来。周作人所关注的食物,多来自乡野或市井,所谓吃的品位在周作人看来并不在于吃的内容,而在于一种自在的人生况味。
比如谈吃螺蛳,“剢去尾巴,加酱油蒸熟,搁点葱油,要算是一样荤菜了。假如再有一碗老酒,嗍得吱吱有味,这时高兴起来,忽然想到强盗若是看见一定也要歆羡的吧。”印证了“剢螺蛳过酒,强盗赶来勿肯走”的民间俗语。和如今夜宵摊上的螺蛳吃法如出一辙,让人读而生涎。
再比如谈吃鱼,“取白鲦较小者,用酱油加酒和花椒煮熟,炭火烘干……风味淡白,可肴可点,收藏在瓷瓶里,随时摸出几条来,不必蒸煮就可以吃,味道总是那么鲜美。”字里行间透露出的更多的是生活的趣味。
一九五一年十二月二十日的《亦报》里,他写到山楂与红果,“煮熟剥皮去核,加糖再煮,并不曾炒,却叫做炒红果”,酸甜可口,是老北京冬天里的念想。
冬日漫漫,外面寒冷有风大作,唯有捧在手中的吃食与对坐言笑晏晏的人儿分外温暖。不如就,热茶暖饭,羊蝎子炒栗子,吃吃喝喝过一冬。
暖锅

乡下冬天食桌上常用暖锅,普通家庭也不能每天都用,但有什么事情的时候,如祭祖及过年差不多一定使用的。一桌“十碗头”里面第一碗必是三鲜,用暖锅时便把这一种装入,大概主要的是鱼圆肉饼子,海参、粉条、白菜垫底,外加鸡蛋糕和笋片。
别时候倒也罢了,阴历正月“拜坟岁”时实在最为必要,坐上两三小时的船,到了坟头在寒风上行了礼,回到船上来虽然饭和酒是热的,菜却是冰凉,中间摆上一个火锅,不但锅里的东西热气腾腾,各人还将扣肉、扣鸡以及底下的芋艿、金针菜之类都加了进去,“咕嘟”一会儿之后,变成一大锅大杂烩,又热又好吃,比平常一碗碗的单独吃要好得多。
乡下结婚,不问贫富照例要雇喜娘照料,浙东是由堕民的女人任其事,她们除报酬以外还有一种权利,便是将新房和客人一部分的剩余肴馔拿回家去。她们用一只红漆的水桶将馂馀都倒在里边,每天家里有人来拿去,这叫作拼拢坳羹,名称不很好,但据说重煮一回来吃其味甚佳云。我没有机会吃过这东西,可是凭了暖锅的经验来说,上边的话,大概不全是假的。
原载《亦报》一九五一年一月二十五日
臭豆腐

近日百物昂贵,手捏三四百元出门,买不到什么小菜。四百元只够买一块酱豆腐,而豆腐一块也要百元以上,加上盐和香油生吃,既不经吃也不便宜,这时候只有买臭豆腐最是上算了。这只要百元一块,味道颇好,可以杀饭,却又不能多吃,大概半块便可下一顿饭,这不是很经济的么。
这一类的食品在我们的乡下出产很多,豆腐做的是霉豆腐,分红霉豆腐、臭霉豆腐两种,(另)有霉千张,霉苋菜梗,霉菜头,这些乃是家里自制的。外边改称酱豆腐、臭豆腐,这也没有什么关系,但本地别有一种臭豆腐,用油炸了吃的,所以在乡下人看来,这名称是有点缠夹的了。
更有意思的是,乡下所制干菜,有白菜干、油菜干、倒督菜之分,外边则统称之为霉干菜,干菜本不霉而称之曰霉,豆腐事实上是霉过的而不称为霉,在乡下人听了是很有点儿别扭的。
豆腐据说是淮南遗制,历史甚长,够得上说是中国文明的特产,现代科学盛称大豆的营养价值,所以这是名实相符的国粹。
他的制品又是种类很多,豆腐,油豆腐,豆腐干,豆腐皮,千张,豆腐渣,此外还有豆腐浆和豆面包,做起菜来各具风味,并不单调,如用豆腐店的出品做成十碗菜,一定是比沙锅居的全猪席要好得多的。中国人民所吃的小菜,一半是白菜萝卜,一半是豆腐制品,淮南的流泽实是孔长了。
还有一件事想起来也很好玩的,便是西洋人永不会得吃豆腐,我们想象用了豆腐干油豆腐去做大菜,能够做出什么东西来,巴黎的豆腐公司之失败,也就是一个证明了。
原载《亦报》一九四九年十二月二十六日
猪头肉

小时候在摊上用几个钱买猪头肉,白切薄片,放在干荷叶上,微微洒点盐,空口吃也好,夹在烧饼里最是相宜,胜过北方的酱肘子。
江浙人民过年必买猪头祭神,但城里人家多用长方猪肉,屠家的专名是元宝肉,大概因为新年置办酒席,需用肉多的缘故,所以在家里就吃不到猪头。
北京市上售卖的很多,但是我吃过一回最好的猪头肉,却是在一个朋友家里。他是山东清河县人氏,善于做词,大学毕业后在各校教书,有一年他依照乡风,在新年制办馒头猪头肉请客,山东馒头之佳是没有问题的,猪头有红白两样做法,甘美无可比喻。
主人以小诗二首代柬招饮,当时曾依韵和作打油,还记得其一的下两句云:早起喝茶看报了,出门赶去吃猪头。清河名物,据主人说此外还有“臭水浒”,清河人称武松为乡亲,所以对于《水浒》似乎特别有兴趣,喜欢说,无论讲哪一段都说得很黄色,因此得了臭名。
这本是禁止的,可是三五人在墙根屋角,就说了起来,这是很特殊的一种说法,但若是把《水浒》当作《金瓶梅》前集看时,那么这也是可以讲得过去的吧。
原载《亦报》一九五一年二月十一日
带皮羊肉

在家乡吃羊肉都带皮,与猪肉同,阅《癸巳存稿》,卷十中有云:
羊皮为裘,本不应入烹调。《钓矶立谈》云,韩熙载使中原,中原人问江南何故不食剥皮羊,熙载曰,地产罗纨故也,乃通达之言。
因此知江南在五代时便已吃带皮羊肉矣。大抵南方羊皮不适于为裘,不如剃毛作毡,以皮入馔,猪皮或有不喜啖者,羊皮则颇甘脆,凡吃得羊肉者当无不食也。北京食羊有种种制法,若箭门内月盛斋之酱羊肉,又为名物,惟鄙人至今尚不忘故乡之羊肉粥,终以为蒸羊最有风味耳。
羊肉粥制法,用钱十二文买羊肉一包,去包裹的鲜荷叶,放大碗内,再就粥摊买粥三文倒入,下盐,趋热食之,如用自家煨粥更佳。吾乡羊肉店只卖蒸羊,即此间所谓汤羊,如欲得生肉,须先期约定,乡俗必用萝卜红烧,并无别的吃法,云萝卜可以去膻,但店头的熟羊肉却亦并无膻味。北京有卖蒸羊者,乃是五香蒸羊肉,并非是白煮者也。
选自《书房一角》
山楂与红果

读了江幼农先生讲山楂的文章,真觉得有点馋起来了,因为我是爱吃酸甜的东西的。
可是读完了的时候也不免失望,因为他遗漏了一样物事,这便是北京水果店里所必备的炒红果。
我在乡下的时候,吃过山楂糕,方言只叫做楂糕,也吃冰糖葫芦,叫做糖山球,我知道这都是用红果所做的,国语则云山楂。
北京的冰糖葫芦很有名,比乡下的做得好多了,有些中间嵌核桃或豆沙的,我却并不赏识,以为还是那简单用红果做的好。
炒红果则只是北京有,我觉得很好,虽然假如自己家里来制造自然还要好,至少是会软得多。这同冰糖葫芦用的是一样的材料,煮熟剥皮去核,加糖再煮,并不曾炒,却叫做炒红果。这红果的名称也是与乡下方言相合的,北京普通称为山里红。
在乡下另有一种,叫做山里果子。与红果不同,个子较小,形如算盘子,山里人用线穿成大小各串,在街上叫卖。
我以前一直把这当作山楂,看药店里所用的山楂也正是这个,并不是大个的红果。这种山里果子在北京似乎没有,就只不曾去请教药店,不知道他们用的是哪一种。《本草纲目启蒙》中引各医书中名称,有山果子、映山红果、糖球儿、糖球子、棠球子各种,仿佛与山里果子、红果、糖山球各俗名都有关系的样子,又有山栗红果与山栗果两名,我颇怀疑第二字有误,如写作里字就正好了。这末了两个名字据说出于《古今医统》。
原载《亦报》一九五一年十二月二十二日
炒栗子

日前偶读陆祁孙的《合肥学舍札记》,卷一有《都门旧句》一则云:
往在都门得句云:“栗香前市火,菊影故园霜。”卖炒栗时人家方莳菊,往来花担不绝,自谓写景物如画。后见蔡浣霞銮扬诗,亦有“栗香前市火,杉影后门钟”之句,未知孰胜。
将北京的炒栗子做进诗里去,倒是颇有趣味的事。我想芗婴居士文昭诗中常咏市井景物,当必有好些材料,可惜《紫幢轩集》没有买到,所有的虽然是有“堂堂堂”藏印的书,可是只得《画屏斋稿》等三种,在《艾集》下卷找到《时果》三章,其二是栗云:
风戾可充冬,食新先用炒。
手剥下夜茶,饤盘妃红枣。
北路虽上番,不如东路好。
居士毕竟是不凡,这首诗写得很有风趣,非寻常咏物诗之比,我很觉得喜欢,虽然自己知道诗是我所不大懂的。
说到炒栗,自然第一联想到的是放翁的笔记,但是我又记起清朝还有些人说过,便就近先从赵云松的《陔馀丛考》查起,在卷三十三里找到《京师炒栗》一条,其文云:
今京师炒栗最佳,四方皆不能及。按宋人小说,汴京李和炒栗名闻四方,绍兴中陈长卿及钱恺使金,至燕山,忽有人持炒栗十枚来献,自白曰:“汴京李和儿也”,挥涕而去。盖金破汴后流转于燕,仍以炒栗世其业耳,然则今京师炒栗是其遗法耶。
这里所说似乎有点不大可靠,如炒栗十枚便太少,不像是实有的事。其次在郝兰皋的《晒书堂笔录》卷四有《炒栗》一则云:
栗生啖之益人,而新者微觉寡味,干取食之则味佳矣,苏子由服栗法亦是取其极干者耳。然市肆皆传炒栗法。余幼时自塾晚归,闻街头唤炒栗声,舌本流津,买之盈袖,恣意咀嚼,其栗殊小而壳薄,中实充满,炒用糖膏则壳极柔脆,手微剥之,壳肉易离而皮膜不粘,意甚快也。及来京师,见市肆门外置柴锅,一人向火,一人坐高凳子上,操长柄铁勺频搅之令匀遍。其栗稍大,而炒制之法,和以濡糖,藉以粗沙亦如余幼时所见,而甜美过之,都市炫鬻,相染成风,盘饤间称佳味矣。
偶读《老学庵笔记》二,言故都李和炒栗名闻四方,他人百计效之,终不可及。绍兴中陈福公及钱上阁出使虏庭,至燕山忽有两人持炒栗各十裹来献,三节人亦人得一裹,自赞曰李和儿也,挥涕而去。惜其法竟不传,放翁虽著记而不能究言其详也。
所谓宋人小说,盖即是《老学庵笔记》,“十枚”亦可知是“十裹”之误。郝君的是有情趣的人,学者而兼有诗人的意味,故所记特别有意思,如写炒栗之特色,炒时的情状,均简明可喜,《晒书堂集》中可取处甚多,此其一例耳。
糖炒栗子法在中国殆已普遍,李和家想必特别佳妙,赵君以为京师市肆传其遗法恐未必然。绍兴亦有此种炒栗,平常系水果店兼营,与北京之多由干果铺制售者不同。案,孟元老著《东京梦华录》卷八,《立秋》项下说及李和云:
鸡头上市,则梁门里李和家最盛。士庶买之,一裹十文,用小新荷叶包,糁以麝香,红小索儿系之。卖者虽多,不及李和一色拣银皮子嫩者货之。
李李村著《汴宋竹枝词》百首,曾咏其事云:
明珠的的价难酬,昨夜南风黄嘴浮。
似向胸前解罗被,碧荷叶裹嫩鸡头。
这样看来,那么李和家原来岂不也就是一爿鲜果铺么?放翁的笔记原文已见前引《晒书堂笔记》中,兹不再抄。三年前的冬天偶食炒栗,记起放翁来,陆续写二绝句,致其怀念,时已近岁除矣,其词云:
燕山柳色太凄迷,话到家园一泪垂。
长向行人供炒栗,伤心最是李和儿。
家祭年年总是虚,乃翁心愿竟何如。
故园未毁不归去,怕出偏门过鲁墟。
先祖母孙太君家在偏门外,与快阁比邻,蒋太君家鲁墟,即放翁诗所云“轻帆过鲁墟”者是也。案,《嘉泰会稽志》卷十七草部,荷下有云:
出偏门至三山多白莲,出三江门至梅山多红莲。夏夜香风率一二十里不绝,非尘境也,而游者多以昼,故不尽知。
出偏门至三山,不佞儿时往鲁墟去,正是走这条道,但未曾见过莲花,盖田中只是稻,水中亦惟有大菱茭白,即鸡头子也少有人种植。近来更有二十年以上不曾看见,不知是什么形状矣。
廿九年三月二十日。
原载《中和月刊》一九四〇年一卷六期
内容选自: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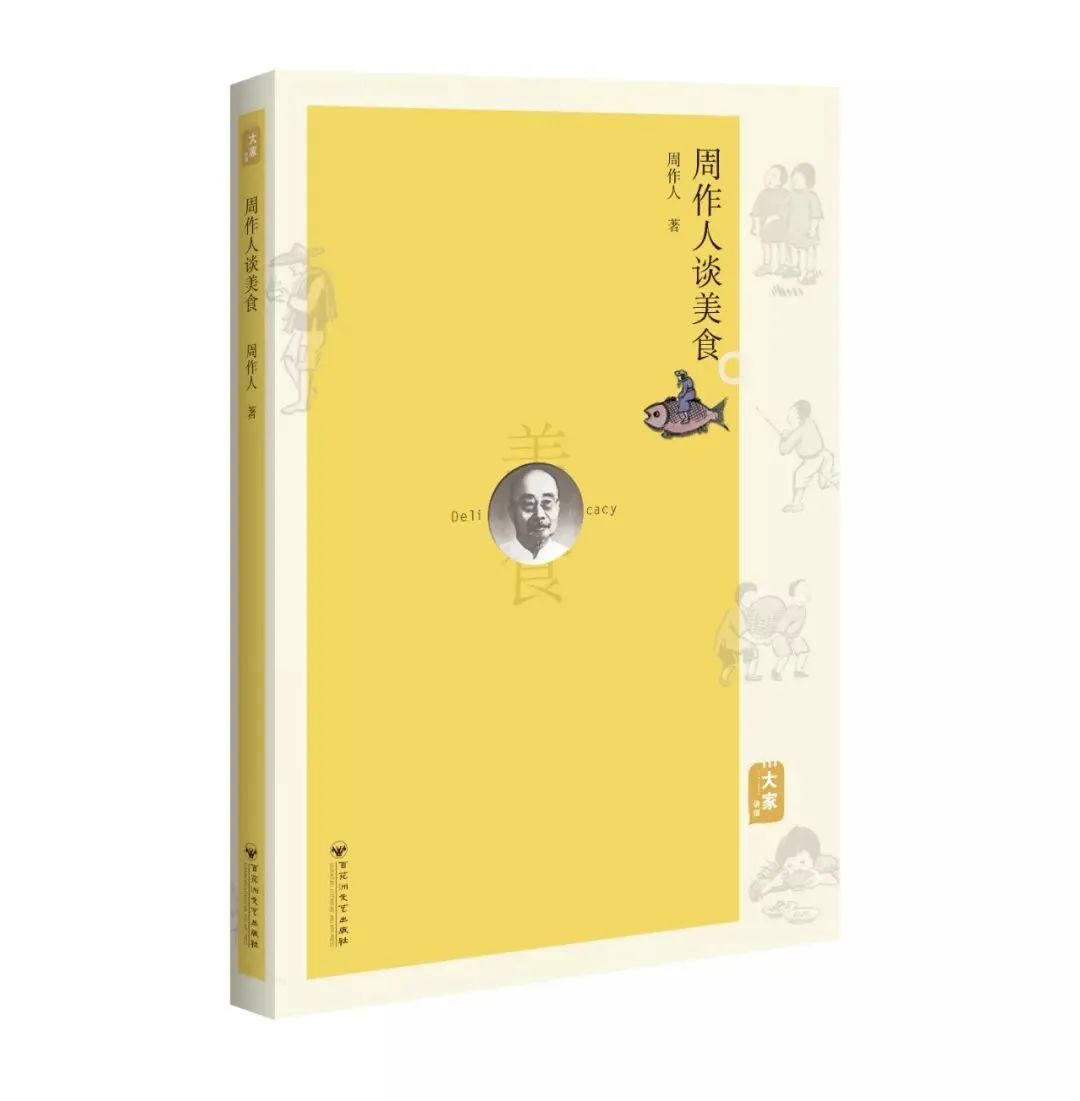
《周作人谈美食》
周作人 著
百花洲文艺出版社
2019年12月出版
郑重声明:本文版权归原作者所有,转载文章仅为传播更多信息之目的,如作者信息标记有误,请第一时间联系我们修改或删除,多谢。



